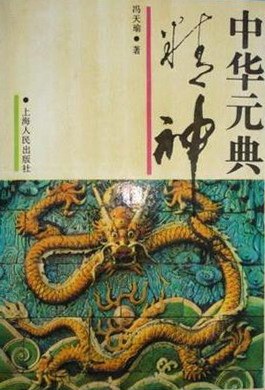
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,东地中海沿岸、南亚次大陆、东亚大陆的几大古文明,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精神飞跃时期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“轴心时代”,也即人类精神枢轴形成的时代。轴心时代的一个显著成果,便是先哲历经数代锻冶,构建观照宇宙、社会、人生的文本,成为延传后世的经籍,笔者曾将其称为“文化元典”(参见拙著《中华元典精神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),堪称“元典”的论著略如下述——
希伯来的《旧约全书》《新约全书》;
古希腊的柏拉图《美诺篇》《巴门尼德篇》《理想国》,亚里士多德《工具论》《物理学》《形而上学》等群哲论著;
古印度的《吠陀》及承续其绪的《梵书》《森林书》《奥义书》,以及由“经藏”“律藏”“论藏”组成的佛典;
中国先秦的“五经”(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),以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诸书。
文化元典提供第一批原创性理念与范畴,构筑诸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家园。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、后人思想运行的基轴和腾跃的起跳板,元典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。英国科学哲学家怀特海说:“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。”可见西方人对其元典的依凭。中国哲人张载说:“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王夫之说: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,将作为“往圣绝学”的元典(如六经)视作开辟“万世太平”的精神起点。
“六经”乃中华元典的基干,而“乐”本无经,传之后世的实为“五经”。“五经”是殷周王官的集体创作,流传数百载,由下移民间的晚周诸子(如孔子及门徒)修纂成册。春秋末年的孔子(前551—前479)并非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的著作者,而是整理者、阐述者,“述而不作”即此之谓。孔门再传弟子追记孔门师徒言行,成《论语》一书。
《论语》成书于战国初年,恰值“五经”编纂、集成的关键时段,也是诸子成书前夕,故《论语》上承“五经”,下启战国诸子。诸子书多与《论语》保有因缘关系:或者发扬其遗绪(如《孟子》《荀子》),或者与其展开辩难(如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)。因此,《论语》处于中华元典的枢纽位置,其着力阐发的仁学与礼学,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,对于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发挥了重大影响。
与印度元典、希伯来元典不同,《论语》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宗教色彩淡薄,并且很少玄谈“性与天道”,不大正面言及哲学本体论、宇宙论,其探讨的多是平实的人生哲理,将“五经”要义包蕴于日用常行之中,论仁、论义、论礼、论智、论信、论孝悌、论君子,寓大道于人伦,自成一种非神文的人文思想系统,这是《论语》智慧的特色所在。通过《论语》的解读,能够加深对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的认知,有助于把握其优长与缺失。
元典作为蕴藏着丰富文化基元的文本,预留无限宽阔的诠释空间,具有常释常新的潜能。《论语》弦诵之声不绝千古,世世代代的人们在阅读间发出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的赞叹。千百年来,《论语》的注解及诠释本多不胜举,如今,张艳国教授著《〈论语〉智慧赏析》,把握住中华元典的人文要义,并以新锐的现代意识观照,从人生哲学入手,旁及政治观、社会观、教育观,纲举而目张。该书从《论语》的语录体风格出发,采取逐段解析的方式,提炼各篇主题,予以凝练概括,拟就的一些小标题,不失原义,又用语鲜活,富于时代性和感染力。通过“与古人对话”,把原文所蕴智慧提炼出来,展现先哲的现代启示,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,展示了新的学术视角。(冯天瑜)



fbdf33fc-de5a-4e45-bf48-2cd4f7e58db0_zsize.png)
3eecf016-e295-454c-ae86-b956c090fa65_zsize.png)
0c00ce37-bf23-4312-9a19-887746784a2a_zsize.png)
ff14ead1-5094-44e3-9800-4a4e32ef88ba_zsize.png)




